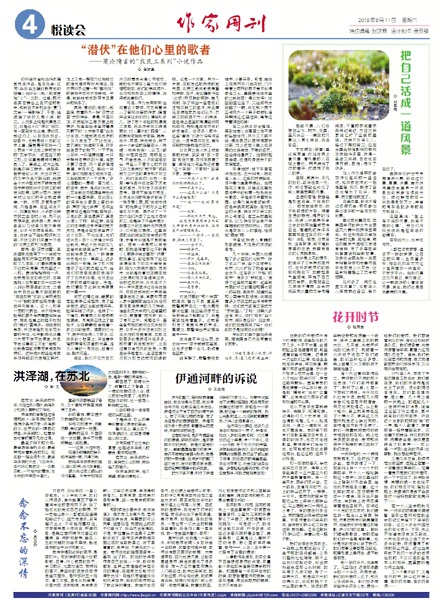
“潜伏”在他们心里的歌者
“潜伏”在他们心里的歌者
——简论隋言的“农民工系列”小说作品
黄哲真
初识吉林省知名作家隋言先生作品,是在当年《辽河》杂志白主编约我写他的短篇小说评论(《知人知面更知“心”》)之时。过后,既然是其它舞台上受欢迎的歌手,那就自然有机会在《厦门文学》一展歌喉了,于是,陆续编了他的几篇小说、散文。从关系上说起来算是文友,只是迄今仅“神交”而已,有一回到东北出差,想约见,却没约上,以后当找机会。印象中,也就是说从他的文字上看,隋言属于那种一门心思在一片土地上耕耘劳作的“文学农夫”,这在当下的文坛,应该算是精神可嘉的良人了。事实上,这片土地,就是农民工群体。说起来,自新世纪以来,关注农民工的文学作品不断出现,就跟各个大中型城市不断制定倾向于照顾和关怀农民工的规定与政策,如积分落户、指定学校让他们的子女就读等等,一样。然而,尽管角度不同、风格各异,而且深浅不一,与隋言相比,大多数反映农民工生活的小说,先不谈思想深度,就体察入微、关怀备至以及设身处地方面而言,似乎与之颇有差距。为此,在综合下结论和评判之前,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农民工系列”作品吧。
首先,是《芬芳如雪》,具体细微地描写了一个在城市里拾荒和打杂工的老农,撷取了几件在人们看来再普通不过的平常事,来刻画这个人物。要说稍稍特别一点,也就是他在收破烂时,在某高档小区帮着救助一位因与人纠纷而昏倒的女士,之后由于自己丝毫不图回报的“英雄救美”式的义举而受到“VIP”般的独家拾荒待遇(但他并未接受)。这个人物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同样做拾荒的妻子有病需要住院治疗,因此他肩上的担子比别的“同行”重得多。但困苦和卑微,并没有挫败他乐观乐善的天性,也未影响他只靠力气而不贪不捡便宜、并且专做好事而又不敢“逾矩”,也就是因做好事而享受某种特权。这种纯朴的品性与其乐观开朗的天性相互映衬,加上又有一帮同为收购破烂的难兄难弟帮衬与同乐,自然两口子过着一种“甜滋滋”的苦日子而并不觉苦呵。于是,就能够感觉到芬芳且清白的快乐了。
再来,看他的《跑街》,那里面,有着另外一种“芬芳如雪”式的快乐。清晨,风雪交加,农民赶车工老瓦套上破棉袄,检查车胎准备顶着漫天飘下的“小米糁子雪”出车讨生活,大腿却被他五岁的小女儿抱住了,不让他走。老瓦连忙“快速躬下身,两手掐住囝子的腋下,一下子抱入怀中,一只胳膊托着,一只手解开老棉袄的大襟,将囝子裹了进去,两个箭步走进屋里,冲向床边,腾出一只手,急切地把她放进被子里,又轻轻地掖了一下被角。”多么温馨的一幕呵!更为感人的在于,囝子,是他们夫妇二人五年前在马路隔离带捡来的一个豁唇弃婴。那位狠心的妈妈在女婴身上留的字条,声称“无力供养”,恐怕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豁唇残疾,又是女孩,索性遗弃了,真是太狠心了呀!就这样,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老瓦夫妇,愣是含辛茹苦留养了这个女孩。不光如此,他们还决定从自个儿牙缝之中挤出钱来,带这个捡来的女儿去省城做修复治疗手术,使她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事实上,这多出来的一张嘴,除了极大地增添了他们的负担之外,给他们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也滋生出了新的希望和追求。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充满暖意的一幕——
老瓦边喝边说,蜡黄的老脸渐渐红润起来,有了些许生动,皱纹全部舒展开来,脸面平阔了许多。他抹了一下嘴巴,朝着吴三珍孬唧唧地傻笑。月亮早已爬上了窗格子,似在静静地偷窥着一家三口的世界。橘黄的灯光下,囝子已经进入了梦乡,红扑扑的小脸蛋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和孩童的天真,涎水从嘴的一角流出,扯着长线,酣然可爱。
在此,我们不仅为老瓦夫妇的善良与爱心所感动,同时也不禁在心里为他们祝福和鼓劲,他们的单纯质朴、乐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
可是,作为长期默默注视着这个群体、对之有着深入了解和体察的作家,隋言并没有让我们的心情轻松多久。除了那个年轻时既漂亮又性感,而且泼辣而又随遇而安、讨人喜欢的“四嫂”,从四哥到老抽到于老鸹,离异、丧夫、同居,转来转去,转不出一个命运的怪圈而令人唏嘘(《转来转去》),以及《断翅》中老实巴交、有的是力气,热爱生活、从不向困难低头,并且从不愿亏心的农民工孙三生夫妇“城市梦”破碎而为之产生的凄凉和不甘之外,我们在他的《纷扬》《布局》等作品中体验到了沉甸甸的感觉,并引发了深深的思考。疑问不禁油然而生。孙三生夫妇的形象折射出了一种矛盾心理,即“向城市进军”的无奈之下的对乡土的眷恋与不舍。虽然点了一下交代他们失去了土地才进城打工,但是除了作品中展示、披露之外的生存状况所提甚少,仅可略见端倪。这里面透射出的被迫改变命运的艰难、矛盾与纠结是不言而喻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随着那位不时靠小心眼挣点钱的鄙称“妖精”的张寡妇,到运粮车下捡扫渗漏在车下的玉米等粮食时,因为大车突然启动,向后方,也就是张寡妇正跪在地上捡漏的地方急速倒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孙三生才大叫一声并且猛冲过去将她推开,而自己却咣的一声被车撞倒在地之后,其妻彩萍嫂从家中壁橱取出他们夫妇俩累死累活挣得的几万块钱,准备救丈夫命的几近绝望的状态,眼看着“城市梦”碎入了寒风之中。问题在于,据笔者所知的城市近郊失地农民,似乎大多并没有如孙三生夫妇的艰苦局面,反而见到更多的是拆迁补偿多多,即所谓“拆迁即发财”,之后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大概是由于笔者本人生活在吉林与较大较发达城市的缘故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在较发达较先进的城市里,农民工愈来愈受尊重和照顾,当然,诚如隋言作品《纷扬》所反映的那样,曾几何时,除了相当一些老板们狂榨农民工的血汗,并且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以外,农民工的疾苦不为人们关注,在社会上甚至时常遭到白眼和歧视,特别是往往对他们缺乏信任。在很多人眼中,这些“盲流”们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一旦有案件发生,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农民工。
女农民工在火车上被查票的时候,紧紧将“那个东西”抱在怀里,女列车员看了看,便问她为何坐车还抱着“这个东西”,不累呀?回答不累。接着——
——那是什么呀?我看你的眼睛都熬红了。
——不是什么。
——这是什么话?不是什么是啥意思?
——我——我的票有问题?
——没有。
——那就别问了,同志。
她感觉周围有许多双目光带着热度向她射来,车厢里开始囔囔起来。
——一个盒子,一直抱着,都走几百里了。
———金子呗。
——银条呗。
——神经病。
——不对,是毒品。
——毒品还用抱着?
——怕抢。
——贩毒是犯罪。
——有人不怕犯罪。
——是炸药。
——是雷管。
——扯淡。
对她怀里的“那个东西”的猜测,皆为不良,直至男乘警闻声走近,一脸冰霜地要求检查,她已经如惊弓之鸟般完全不能配合了,只是更紧地抱着盒子。这就更引发了周围斥责的声浪。高潮处,乘警伸出手欲强夺盒子——
她将盒子举过头顶,哀求说——“孩子爸爸在里面,让他多安静一会儿,我领着他回家。”
谜有解了,乘警触电般缩手,众意平息。可是,当她上完厕所开门出来时,门外等着上厕所的男子竟然长得像包工头,莫非要将她手里的工钱抢回?是幻觉吗?她回到座位坐下,又往厕所方向瞄了一眼,只见那个男子正与另外一个男子窃窃私语并朝她这边望过来,嘴角还带着阴险的笑!
包工头缺乏安全措施,导致她老公在高层工地干活时坠楼惨死;另外又欠薪不给,逼她自己以自焚相要挟讨薪,加上这在火车上受凌辱的这些痛苦、不堪的经历,已经将她逼疯了。她顿时起身后退,迅速转身往另外的车厢跑去。
车停站时,她下车冒雪冲向空地,边大叫有人抢劫有人杀人,边跑的时候摔倒,怀中骨灰盒撒手丢出。她爬起来又滑倒,只能坐在雪地里将手中的钞票一张张向空中撒去。于是纸币与雪花共舞。这是为其夫撒纸钱呵!这是命换来的真钱,是对社会的冷漠、缺乏对农民工的关心与信任、包工头的盘剥欺负,以及缺乏安全生产保障措施的悲愤的抗议。同时也是女主人公的懊悔,悔进城“掘金”啊!
作者这种透入骨髓的形象塑造,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几十年来,中国大地崛起了多少座现代化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各个区域中心城市,大大扩张了的各省省会之外,还有多少“升格”的城市?有多少“新城里人”涌进了这些城市里面?这些城市里的林立的高楼和横七竖八的马路、高架桥、隧道桥梁和公园等市政设施,该凝结着多少农民工的血汗与辛劳啊。他们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新城里人”了吗?如果大多没有,那么,他们“转战”各个城市,何日是归日?归去后,他们的田园荒芜了吗?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呢?
无论我们能不能给出答案,相信隋言仍然在写着他们的歌。
(作者系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原《厦门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