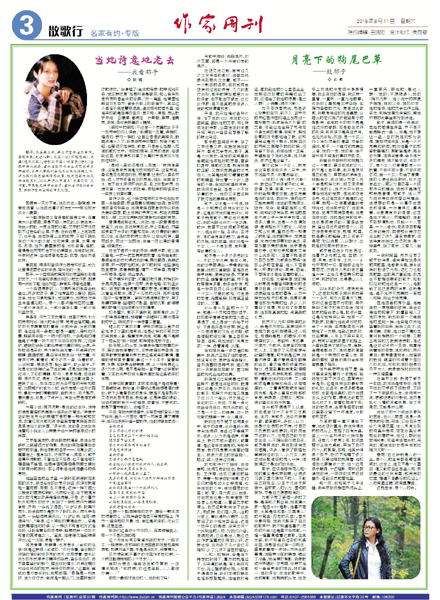
当她诗意地老去
当她诗意地老去
——我看郁子
默 梅

郁子:本名李玉环,毕业于吉林省文学院。著有诗集《走过人群》,长篇小说《不想随缘》,文集《随风沉默》。诗歌及中篇小说曾获《诗刊》全国新诗大奖赛、吉林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等多种奖项。多年从事报刊杂志及出版社编辑工作,并为报刊杂志撰稿情感故事、散文随笔专栏及做话题策划。2005年于北京建立“浅草花田”工作室。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吉林文化馆。
即便有一天放下笔,她依然在人群背后,诗意地活着,以她自己喜欢的方式——哪怕那方式令人瞠目。
一个酗酒抽烟又有洁癖的单身女子,在庸常大众的眼里,原是不招人待见的。纵使她有一张出众的脸,一支生花的妙笔,文字的芬芳终究敌不过世俗的尘烟。于是,在传统意义上她陷落了。也于是,她在杂草丛生的地带,不屈不挠地生成一片大的水域,放牧诗情,亲情,友情,音乐,孤独。当然,最重要的是,放牧爱情。是的,爱情是她死死叼住不放的黑面包。年轻时这样,中年时这样,当她诗意地老去,我想,她依然是这样。
事实是,啤酒和香烟作为符号和标签,成为比爱情还要忠实的伴侣,陪伴她的一生。
郁子,一个在烟酒的围困和救赎里释放激情的女子,一个用爱和疼痛创作的小城女作家。即便有一天放下笔,她依然在人群背后,诗意地活着。
一个条理清晰的人,习惯所有的东西各就各位。两岁的孩子,拿了她房里的小摆设,把玩之后,她也习惯地指引,放回原处。如同她对待生命里遇见的人,每个人都占据相应的位置,“一部分写在纸上,一部分留在心里,一部分在风里弥荡。”
早些年,作为文艺女青年,她喜欢宽松长大的棉布衬衫,阔大的牛仔裤,稀奇古怪的鞋。柔软的长发肆意地打着卷,纷披开去,冷寂的眉眼,走在任何一条街口都是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胸前常年挂一个硕大的饰物,一条略粗的褐色绳子吊着一块木非木石非石的东西,刀刻斧砍,硬朗的线条勾勒出异域风情的神秘头像。半张脸却是平的,另外半张突兀着一只奇异的大眼睛,圆圆鼓鼓,莫名惊诧地生出一股力量,与世界对峙。戴着它,郁子孑然一身,沿着铁轨,从北到南,漂泊游荡,抬头望天,低头写字。不知是它的独特成全了她的美,还是她的特立独行深入了它的精髓,物与人息息相通,彼此映照,浑然天成。偶有人好奇地拿过去戴在身上,更换了主人,那东西立时失去所有的光彩和魅惑。如同粗犷的北方小城,突然造起一座苏式园林,景致一样的精雕细琢,曲桥流水,花木繁茂,看来看去,总是少了点什么。有些光芒是相互辉映的。
中篇小说《随风沉默》是她的成名作,独特的语言营造的氛围至今读来依然着迷。“荞麦子姑的脸在月光的照耀下呈现着一种忧郁和孤独。我看见那忧郁和孤独里面有着某种高贵而且温凉如水的东西。”多年来,她的身上始终流淌着和小说主人公荞麦子姑一样的温凉如水的东西。
文字是温凉的。像她眼底的清澈,像她坐在铁轨上眺望远方的背影,像她的深陷爱情饱尝悲欢的手温。像她诗歌的名字——《月亮女孩》,高高在上,温凉如水,仿佛不食人间烟火。郁子是属于诗歌的,不管她写不写诗,也不管她喝不喝酒抽不抽烟。如果啤酒和香烟是两根支撑她不断前行的拐杖,那么诗歌是她灵魂最终的栖息地。
她幽蓝色的血液里,一股时而低缓时而激越的流水,穿过俗世的纷争与纠结,孤独而执著地一直向前,向前,永不停息。这样一种不被大众接受的理想和期盼,沉溺和沦陷,终于把温凉如水的月亮女孩弄得遍体疲惫。于是,这个喜欢秋天和雨水的女子,找到了一种物质作为精神食粮,然后,一头扎了进去。“20岁以后,我离开雨水。我深信雨水是救不了我的。我从雨水中走出来,一头钻进啤酒深处。”30岁以后,她写《啤酒深处》,“啤酒,这个神秘的黄褐色女人,总是在我需要她的时候,以一种妙不可言的方式走近我,让我在黄色的波涛中,摇摆成另一位妙不可言的黄褐色女人。”至此,她缓缓沉陷到啤酒深处。这一沉陷,便是一辈子。
她写爱情,写亲情,也写音乐。《全体的母亲》她是这样进入叙述的:“你行走着,音乐把你深陷的足印封进岁月的底片;你思想着,音乐以流水的形式漂净你精神的杂质。音乐走近你,俯下身摩挲你的脑勺,擦去你的泪水,然后在距你可远也可近的地方,等待你的微笑。”这里面,阐述的是对音乐的认知和感悟。“恩雅是一剂良药,她为你疗伤:辛妮是一把尖刀,她重新剥开你的伤口。”由演唱了《全体的母亲》的辛妮说开去,她这样收尾“如果听者是婴孩,那么音乐则是所有听者全体的母亲。”另一篇里,她谦虚地把自己形容为《音乐长街上的街溜子》,其实这个街溜子倒是慧眼独具。浩如烟海的音乐里,她淘来的都是难得的宝贝:居尔特人恩雅,秃头歌手辛妮 . 欧康诺,惠特尼 . 休斯顿,蔡琴,潘美辰,李娜,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
《细雨中的细雨》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女子于一场雨中的内心独白。“我撑起一支篙,诗性的,通透的,新竹一样的,让自己慢慢驶离搁浅。我搁浅得太久了。我像细雨中的植物,即使不能飞翔,也要很好地伸张,或者,只是会心地融入雨滴的敲打之中。”细致的描写,空灵的语言,每读到这里,总觉得那只撑了长篙的手温凉如水地抚过脑际。
《是进入身体还是进入灵魂》:“我相信身体,没有身体灵魂是无枝可栖的鸟;没有灵魂,身体是无鸟可宿的枝。而爱情,让我们从身体开始,进入对方或者自己的灵魂。因此,世间有了水,有了被水深深环绕的岛:岛上枝繁叶茂,鸟语花香!”行云流水的比喻,使枯燥的阅读变成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写作之余,这个抽烟喝酒的女子也抬抬手画一些抽象画。思维里看似粗糙的线条,色彩斑斓或者纯粹黑白,她随意挥洒想象就可以拼出优美的图画,配上独特的手写文字,那些花啊草啊女人啊,立刻充满鲜活的意象和深邃的思想。
爱情是纯粹的私人体验。当一段爱情烟花般湮灭,她说,自己照亮自己。听上去豁达,内里却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和无奈。她对情感的偏执和沉迷,生活状态的特立独行,让世俗和男人望而却步。而她一如既往,在每一场汹涌的爱情里,倾情绽放。
送走了透析十年的母亲,喘息未歇,老父亲又垂危。一夜一夜在病床前熬着,她所能做的,是把白色的药粒喂进他的嘴,帮他翻身,换掉纸尿裤,熬一碗软烂的粥。余下的时间,她坚强地挺直腰背,揉着黑眼圈,喝下一杯啤酒,再喝下一杯啤酒。指间,烟丝缭绕。
郁子唱好听的歌。初夏的微风里,树梢的叶子晃来晃去,她弹六弦琴,低低地唱《耶利亚女郎》,磁性的嗓音透着不羁的野性,寂寞的眼神淡看世间繁华。隔了十几年的光阴,再听她唱《陪你一起看草原》,音响效果很棒的歌厅,带了微醺的醉意,幽暗的灯影里,眉眼沉郁,舒缓醇厚的歌唱沉淀出细腻忧伤的情愫。
初冬雪大,郁子不慎跌倒,脚部骨折。拎了一打啤酒去看她。她翘着一条腿开门,眼光落在我的手上,瞬间孩子一样惊喜又害羞。
腿上打了厚的石膏,肿胀的脚趾上竟然细致地涂了水蓝的指甲油。她是这样的不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指着地中央说,那里,是不是掉了一根头发?拍一拍腿,眼神惆怅地移开去。
捡走地上的头发,除掉绿色植物枯黄的叶子,擦去窗台浮着的灰。左手啤酒右手香烟,她略带歉意地看着我帮忙做这些简单的事情,僵硬的腿脚更觉僵硬。拿过一个小本子,查看电费,水费,取暖费各种票据。咦,上个月电费这么多?为什么呢,是不是电脑一直开着?这样嘟哝着,又在我诧异的目光里快速收起这些琐碎的东西。
她苦恼地看着我,我的脸色是不是很难看?又自嘲地笑,我知道,你要说这是抽烟喝酒的缘故。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身体,腰是不是有赘肉?又很快地自问自答,我知道,这是啤酒的缘故。说话的同时启开一瓶啤酒,接着说,不要笑我。我是不懂节制的人,在嗜好上。
午后,有阳光照进屋子,似有若无的音乐从楼下传来,窗外一片苍茫。喝下一杯啤酒,清了清嗓子,她开始低低吟诵一首新作,《当我诗意地老去》:
当我老去
多么怀念从前的时候
自己能浑身上下一拧一把水地
随便写下些文字
像水中的草和雨中的石子
只是充满情绪
当我老去
已经什么都不愿想起
我会把从小到老对我好的人,挑出来
一部分姓氏写在本子上
一部分人就呆在我心里了
更多的面庞,就让他们在风中鲜活地弥荡
干完这些事情
我就找到最后一个对我好的人
在春日或深秋的午后
坐上一辆回家的马车
一路散漫颠簸,一路慢慢吟诵:
当我诗意地老去……
这样一个酗酒抽烟的女子,握住一颗滚烫的诗意的心,以别样姿态走在不寻常的路上,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她,注定是孤独的。无论文字,还是生活。
而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哪一个不是孤独的呢?
这个与世俗常态背道而驰的女子,一路孑孓,一路踉跄。在琐碎的生活里固执地呈现某种质感,即便风华不再,亦是温凉如水,诗意隽永。
忽然想到郁子喜欢的法国作家杜拉斯,一个疯狂酗酒抽烟的小个子女人。
当时光老去,谁会站在郁子面前,一往情深地说:“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
而那个最后对她好的人,她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