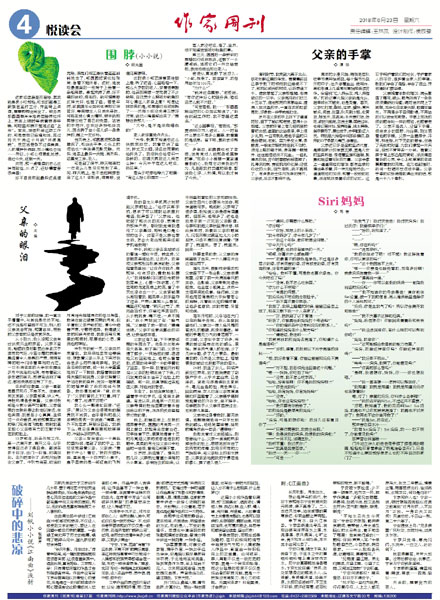
破碎中的悲凉
破碎中的悲凉
——刘帆小小说《江南曲》浅析
张联芹
刘帆先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几十年,善于调动艺术手段来诠释各种体验,无论是生活体验还是心灵体验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都有集中而又完美的展现,所以,他的作品是富有特色而又令人难忘的。
在曲调悠扬中讲述《江南曲》中的感动和悲凉,不仅让人感受到文字的魅力,更让人在回望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一曲望江南拉开了历史的帷幕,唱响了破碎山河中,国仇家恨的悲凉诗篇!
“长风吹影。月华如水。”诗意中起笔,将一幅如歌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置身其中。语言优美,富有特色。文学即人学!只有情感深植的作品才会引起读者共鸣。作品中没有写卞京与若离昭仪刻骨铭心的爱恋,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肢体动作和心理语言让这段情感刻入读者的心中。作品中嵌入古诗词,让作品富有了一种古意、一种诗意,在古意中诠释历史的波光,在诗意中写出“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凄楚悲凉之感,让人唏嘘不已。
风波亭中风不止,对月空怀伤心人!将历史融入其中,可这仅仅是一段历史吗?不,也许作者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而是所有的“破碎山河”,试问,在历史的波澜中有多少破碎,又有多少离合?
“宁安、卞京、若离”有着“汴梁永安、不离不弃”的美好寓意,在这种美好寓意中巧妙地将个人情感和民族荣辱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深邃思考。“南渡、北囚”形成一种距离上的疏离和无奈,让人在品中思、思中悟、悟中感、感中伤!
文学作品的表达技巧有记叙、议论、描写和抒情,而《江南曲》的表达方式却是“另类而又新奇的。” 它通过诗一样的语言让作品具有了形象化和抒情性,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在款款诗意中讲述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恋。夹叙带议,小处着笔,落于高远是这篇作品的又一大特色。
表现手法采用动静结合、虚实相间、点面结合、明暗结合的方式,动的是人,不变的是情怀。在虚化中演绎现实的残酷和情感的疏离,爱憎分明中讲述一种刻骨、一种永恒。
“杂草萋萋间,对襟交领紫裙,褙子外套,一袂女子远处徐徐,似是昭仪脱尽皇家铅华衣装,于北地梅溪间流连。轻抚琴身汴水寻,空上瑶台不见人。尔来梅溪闻客语,犹是故园见血痕。声音由远及近,望江南曲。卞京大恸。”
开门见山、曲笔入题、情节曲折、亦真亦幻。写出一种空间维度,也写出一种时光的回旋,让人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幻!
这篇小小说作品看似简短,却“五脏俱全”,语言动心、情感入肺、表达沁脾,血入肝、精入肾、无开篇、无结尾。从故事情节上来看是完整的,也是可以延伸的,似断非断、藕断丝连,可继续加深,也可戛然而止,将思考和感悟留给读者,留给历史!
梦是美丽的,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在环扣相间的情节中将民族气节和个人情感融入作品中,彰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不仅是一段历史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而这份耻辱的根源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软弱无能,更是一个民族没有凝聚力、向心力的体现。无国何来家?只有国强,才会民安!
附:《江南曲》
长风吹影。月华如水。
想必是神鸟的后代,长衫卞京和布衣宁安前后来到元明坡,便不再走了。二人走进风波亭,站在武穆的真尊身边,似有金鼓之声响起。
亭下有水,曰大江东去。卞京去低洼处寻觅,发现谷底有浮萍在水上漂,水流潺潺,凉风拂面,心旷之余,竟不知水从何处来,亦不觉水往何处去了。
宁安口渴,随之下来,拟俯身下去,于溪水之中打算咕咚咕咚喝上清凉甘洌之水。见宁安真要跪地准备喝水,卞京忙扯住道:“贤弟,此处武穆身边的跪地小人,头被敲,身被唾沫湮,经年不息,水质已经被破坏,不卫生不环保,或许还有毒,这苍松翠柏的地方,断不能喝。”
宁安被卞京扯住,少不得一顿愕然,肠为之一热,拱手作揖道:“多谢兄台提醒,弟愚钝,险被污浊,枉文丞相生死诀《正气歌》赠我,惭愧,惭愧!”
“不知水云先生今何在?”宁安忽然想起,羁押燕京期间,善琴曾入侍太后及昭仪的水云先生,竟不知去了哪里?惟有南归后的《一剪梅·怀旧》声声入耳:“十年愁眼泪巴巴,今日思家,明日思家。……一从别后各天涯,欲寄梅花,莫寄梅花。”
“兄南渡,望江南。弟北归南返,亦望江南。今望了江南,又何如江南哉?”宁安叹道。
“宁安何须感叹?南来惶恐,日日亦不得安宁。”
“兄不知一旦归为臣虏,行行复行行,人上之人都无异鸡犬,比之二帝蒙尘,靖康之难,南宫被掠北行,恰如再版,北地之囚,何日是归年?”
卞京何许人也?宁安一说,顿时想起若离昭仪进宫之前常说“对月伤怀,人不如月”之说。一身功夫又如何?天道茫茫,千云山一别,竟二十六年了。
宁安提剑上马:“兄多保重!”风吹动,剑花对光,如流水乍泄。
卞京只觉得,寒光闪闪,水流中,一应之人,纷纷倒下。
恍若燕塞雪,片片大如拳。没有杨柳依依,长亭边,卞京与宁安就此道别。
卞京跌跌撞撞,嘴里说着:南渡、南渡……若离、昭仪……
天杀的,肆意妄为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