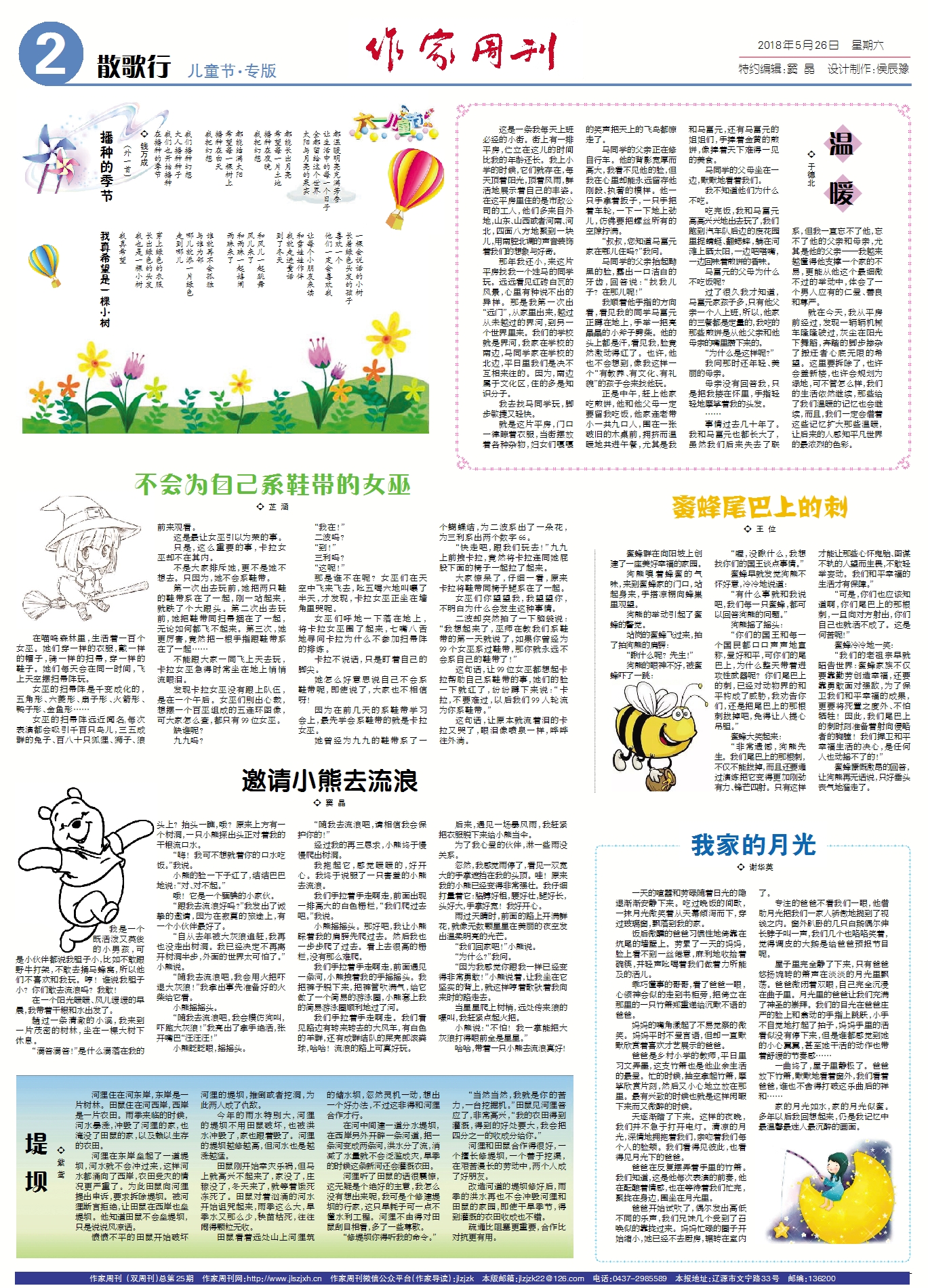
温 暖
温 暖
于德北
这是一条我每天上班必经的小街。街上有一排平房,伫立在这儿的时间比我的年龄还长。我上小学的时候,它们就存在,每天顶着阳光,顶着风雨,鲜活地展示着自己的丰姿。在这平房里住的是市政公司的工人,他们多来自外地,山东、山西或者河南、河北,四面八方地聚到一块儿,用南腔北调的声音装饰着我们的想象与好奇。
那年我还小,来这片平房找我一个姓马的同学玩。远远看见红砖白瓦的风景,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异样。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从家里出来,越过从未越过的界河,到另一个世界里来。我们的学校就是界河,我家在学校的南边,马同学家在学校的北边,平日里我们是决不互相来往的。因为,南边属于文化区,住的多是知识分子。
我去找马同学玩,脚步敏捷又轻快。
就是这片平房,门口一律晾着衣服,当街摆放着各种杂物,妇女们嘎嘎的笑声把天上的飞鸟都惊走了。
马同学的父亲正在修自行车。他的背影宽厚而高大,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在心里却能永远留存他刚毅、执著的模样。他一只手拿着扳子,一只手把着车轮,一下一下地上劲儿,仿佛要把螺丝所有的空隙拧满。
“叔叔,您知道马富元家在哪儿住吗?”我问。
马同学的父亲抬起黝黑的脸,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回答说:“找我儿子?在那儿呢!”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看见我的同学马富元正蹲在地上,手举一把亮晶晶的小斧子劈柴。他的头上都是汗,看见我,脸竟然激动得红了。也许,他也不会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有教养、有文化、有礼貌”的孩子会来找他玩。
正是中午,赶上他家吃煎饼,他和他父母一定要留我吃饭,他家连老带小一共九口人,围在一张破旧的木桌前,拥挤而温暖地共进午餐,尤其是我和马富元,还有马富元的姐姐们,手捧着金黄的煎饼,像捧着天下难得一见的美食。
马同学的父母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我们。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吃。
吃完饭,我和马富元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我们跑到汽车队后边的废花园里捉蜻蜓、翻蟋蟀,躺在河滩上晒太阳,一边吧嗒嘴,一边回味着煎饼的香味。
马富元的父母为什么不吃饭呢?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马富元家孩子多,只有他父亲一个人上班,所以,他家的三餐都是定量的,我吃的那些煎饼是从他父亲和他母亲的嘴里攒下来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问那时还年轻、美丽的母亲。
母亲没有回答我,只是把我搂在怀里,手指轻轻地摩挲着我的头发。
……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我和马富元也都长大了,虽然我们后来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忘不了他,忘不了他的父亲和母亲,尤其是他的父亲——我越来越懂得他支撑一个家的不易,更能从他这个最细微不过的举动中,体会了一个男人应有的仁爱、善良和尊严。
就在今天,我从平房前经过,发现一辆辆机械车隆隆驶过,灰尘在阳光下舞蹈,奔踏的脚步掺杂了搬迁者心底无限的希望。这里要拆除了,也许会盖新楼,也许会规划为绿地,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活依然继续,那些给了我们温暖的记忆也会继续,而且,我们一定会借着这些记忆扩大那些温暖,让后来的人感知平凡世界的最浓烈的色彩。